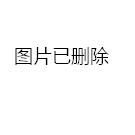 时任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资料图)。
时任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资料图)。
四、坚决抗日
“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梁漱溟应邀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国民政府参议会。会议结束后,蒋介石嘱梁漱溟陪同蒋百里赴山东视察防务。
梁漱溟回到济南向我父亲汇报此事。我父亲说,他已收到蒋介石的电报,知道梁漱溟陪同蒋百里来山东,但不知道究竟来干什么。梁说是蒋介石派他来山东视察防务的。父亲一听就笑了,说:“难道他们还想守山东吗?我认为山东是守不了的,我们打不过日本人。唯一的办法是保存实力,把军队撤到平汉铁路以西,等待国际上的援助,然后再反攻。别的出路没有,欧美是不会让日本独吞中国的。这些道理,蒋介石肚子里比我明白得多,还装什么样子!”
平、津沦陷后,驻北平日本当局曾派特使飞济南,与我父亲谈判。日方提出可以不在山东驻军,但要假道山东运兵。父亲明确表示,不管是驻兵还是运兵,都不允许日军进入山东。
8月20日,日本驻烟台领事馆亦关闭。11月中旬,上海沦陷,南京告急。父亲下令没收日侨财产,在日本洋行内抄出大量枪支、鸦片等私货。他派爆破队到淄博、胶东一带将日本人的厂矿炸毁。
这期间,中共中央毛泽东致信父亲,呼吁建立抗日联合战线,并告之将派同志前往拜谒,“乞赐接谈,如承不弃,予以具体办法”。
父亲采纳了中共中央军委派来的军事联络员的建议,释放了大批在押的共产党干部,并在第三路军成立政训处,举办第三集团军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父亲出任班主任,爱国人士余心清任副主任,北平“左派”文化人主持教务工作。学员主要是平、津流亡学生、山东爱国知识青年及“乡建”派人士,前后共办三期,有一千三百人参加培训。第一批学员五百人于8月底入学,9月中旬被派往临清、德州、惠民、烟台等地开展抗日工作。
1937年9月底,日军沿津浦线长驱直下,兵临鲁境。
第三集团军在津浦线上已集结三师一旅,主力几乎全部压到鲁北,空出的胶东及沿海地区只能由民团填防。
父亲给母亲写信:我部这次与日寇浴血奋战,伤亡惨重,为我从军以来历次战斗所未有,眼见官兵如此伤亡,我心中十分沉重。今后战斗会更加严重,生死存亡,难以预卜。
1937年9月30日,沿津浦线南下的日军矶谷廉介第十师团一部占领冀鲁交界的桑园车站,战火烧到山东的大门口。
10月2日,第三集团军第四八六团夜袭桑园成功。德州守军第八十一师二四三旅四八五团奋力反击。但4日,德州城陷,第四八五团官兵全体为国捐躯。
此后,第三集团军在黄河以北之津浦线上与日军鏖战,历经徒骇河之战、津浦线反击战、临邑之战等役,伤亡惨重。
11月13日,父亲在手枪旅第一团团长贾本甲、副官杨树森、特别侦探队第二大队大队长朱世勤陪同下,率卫士及手枪旅一团二营五连的一个加强排,共七十多人赴济阳前线督战,在济阳西关附近一个村庄,与一支由装甲车队和骑兵部队组成的日军快速突击部队不期而遇。由于敌我战力悬殊,父亲一行寡不敌众,伤亡殆尽,在众卫士拼死掩护下,父亲才突出重围,回到济南。此时,身边只剩下副官杨树森,嗣后又陆续有九名弟兄突围回来,其余弟兄全部阵亡。父亲沉痛地说:“我韩某人能活着从济阳回来,是近六十弟兄的性命换来的。”
五、留下家书
父亲从济阳突围回来,给母亲写了一封亲笔家信,让一位副官专程送到曹县。当时母亲已带着我们兄弟姊妹随后勤机关撤到鲁西曹县。
父亲的信全文如下:
大姐:我部这次与日寇浴血奋战,伤亡惨重,为我从军以来历次战斗所未有,眼见官兵如此伤亡,我心中十分沉重。今后战斗会更加严重,生死存亡,难以预卜。请大姐再勿为我操心,只要把孩子们照顾好,教育好,我即感激之至!现派人送去五千元作为今后之家用,望查收。致安好。向方(韩复榘字向方)
母亲接信痛哭。实际上,这已是父亲的绝笔了。
11月16日,父亲下令全军撤退到黄河南岸。蒋介石从南京打电话令他炸毁黄河铁桥。
第三集团军从1937年10月1日夜袭桑园始,至11月16日撤到黄河南岸止,在鲁北抗战历时一个半月,经过大小战斗十余次,据孙桐萱军长说:“在这次战斗中,曹(福林)、李(汉章)、展(书堂)等师牺牲过半。”
对此,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民国史专家吕伟俊教授在其所著《韩复榘传》一书中,就父亲在鲁北抗战中的表现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从上述抗战以来韩复榘的表现来看,总起来说他还是抗战的,不论其态度是消极或是积极,他还是坚持打了几仗。因此一般史书上称韩‘不战而逃’是不妥当的,也不符合事实。逃在后,战在前。至于传说他想投降当汉奸,就更是无事实根据的。”
第三集团军撤守黄河南岸以后,从1937年11月16日,到12月23日,在此一个月零一周的时间内,战事相对平静。日军偶尔隔河炮击,飞机也来过几次,在济南丢几枚炸弹就飞走了。日机还来过两次空投“通讯筒”,发动“政治攻势”。父亲将日本人通讯筒内的劝降信挂在办公室内示众,以示抗战到底。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来济南视察防务,父亲与他讨论时局及战略问题。当时南京刚沦陷半月,人们记忆犹新,因此黄河防线能否守住,对于李宗仁和我父亲来说已不是问题,他们讨论的关键是,黄河防线一旦被敌突破,第三集团军将辙往何处。李的意思是第三集团军应撤进沂蒙山区,准备打游击。父亲不同意,反驳说:“浦口已失,敌人即将打到蚌埠。他们节节撤退,我们没有了退路,岂不成了包子馅吗!”二人不欢而散。
在父亲看来,将第三集团军赶到山里去打游击的计划不仅极其荒谬,而且别有用心。他认定这是蒋介石利用日本人之手消灭非嫡系部队的一个阴谋。父亲在与李宗仁会晤之后,认为蒋介石既然不肯给他出路,他只有自己找出路了!
此时,李宗仁欲将父亲的炮团调走。
对此,父亲十分气愤。他对何思源说:“蒋叫我们在山东死守黄河,抵住日军,原说派重炮支持的,到快用的时候,忽然抽调走了。他们不守南京,却叫我们死守济南,叫我们用步枪跟日军拼吗?”
李宗仁对此也十分气愤,认为父亲没把他这位司令长官放在眼里。
经过历时一个半月的鲁北作战,父亲深感自己的部队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战斗力,都与日军相去甚远。他认为,在长期抗战之大战略下,与其死守黄河,悉数被歼,不如有计划撤退,保存实力,以利再战。
实际上,父亲早就持有“中国抗日必须西撤而后反攻”的战略思想。他曾向视察山东防务的蒋百里明白表示:对日不求现在决战,但求能战能退,中国军队必撤至平汉线以西,待得到国际援助后,再反攻过来,方能取胜;如目前即进行决战,徒供牺牲,不如暂时保存实力,以待来日。这一观点与蒋百里关于我们的国防线应以“三阳(洛阳、襄阳、衡阳)线”为准的理论不谋而合。
父亲的战略思想应该是没问题的,事实证明,此后八年抗战的发展轨迹也大抵如此。但是,战略决策是大本营的事,父亲虽位尊战区副司令长官、集团军总司令,也不过是一名高级战地指挥官,必须服从大本营的指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无论有什么理由,也必须服从大本营的命令。蒋介石后来欲置他于死地,其实用不着劳神费力,拼凑什么“五大罪状”,仅以“不尊命令,擅自撤退”一条,就足以置他于死地。
六、与李宗仁的矛盾日深
济南危急时,父亲令山东省府由宁阳再迁往曹县,将弹药、给养等军需物资、军医院、修械所、伤病员及官佐眷属用火车运送到河南漯河、舞阳、南阳等地。火车过徐州时,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来电阻止,责问:“豫西非第三集团军的后方,为何运往该地?”父亲随手在电报上批曰:“全面抗战,何分彼此。”又云:“开封、郑州亦非五战区后方,为什么将弹药、给养存在该地?”父亲的参谋处不知是何居心(参谋处有蒋系特务,如联络参谋王道生等,意在挑拨父亲和李宗仁的关系),竟按他随手所批字句,直接电复五战区长官司令部,事先也未将复电呈父亲过目。李宗仁接电,大怒,将父亲之复电直接转给蒋介石。
父亲在电文上信手写批语是他长年军旅生涯养成的习惯,多为有感而发,并非正式复电电文。冯玉祥也有如此习惯,有时看到不合意的文电,批语更是出奇,如:“放屁”“放狗屁”“脱裤子放屁”等,不一而足。
在经过一个多月的相对沉寂之后,日军决定对济南发动攻击。
很快,第三集团军两面受敌,父亲通过电话向李宗仁请求调五十一军于学忠部支援济南,遭到李宗仁的拒绝。
父亲气愤至极,他认为这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大本营以抗战为名,消灭异己的诡计之一,于是再无心恋战,决计引军西撤。
父亲命令孙桐萱第二十师留守济南断后,第三集团军其他各部向泰安、兖州方向撤退。
27日晨,日军占领济南。在济南战役中,第二十师伤亡营长五人,连、排长30余人、士兵1500余人;手枪旅第一团伤亡连、排长10人、士兵300余人。
父亲离开济南后,李宗仁电令其死守泰安。父亲又在来电上信手批了八个字:“南京不守,何守泰安。”参谋处故伎重演,仍将父亲所批字句当作复电,直接拍发给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李宗仁接电,大怒,将电文转给蒋介石,指责父亲不听指挥,擅自行动。
不得不承认,我父亲拒不执行“死守泰安”的命令是犯了一个致命错误。
一个月前,李宗仁、白崇禧还反对守南京,李宗仁甚至主张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李宗仁认为,蒋介石死守南京,是他犯的第二个错误,而第一个错误是死守上海。李说“无奈蒋先生不此之图,意气用事,甚至溃败之兆已显,他还要一守再守,终于溃不成军。试问在长期抗战的原则下,多守一两日和少守一两日,究竟有多少区别?但是在用兵上说,有计划的撤退和无计划的溃败,则相去远甚。”李宗仁言之有理,掷地有声,至于一个月之后他为什么又认为“死守泰安”非但不是“第三个错误”,而且必须贯彻执行不可,自有他的道理,或许泰安“多守一两日和少守一两日”区别很大,第三集团军“有计划的撤退和无计划的溃败”相去不远了。
父亲作为一名战地指挥官,对上级的命令,应该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否则,你说没必要死守,他说有必要死守;你说他借刀杀人,他说他没借刀杀人,这个仗还怎么打?
父亲不听指挥,李宗仁又告他“御状”,况且又是以“抗战”的名义,这对蒋介石来说是绝好的时机。
蒋介石指责我父亲丢了山东。父亲毫不客气地顶撞说:“山东丢失是我的责任,南京丢失又是谁的责任呢?”
李宗仁拿着我父亲的那些电文,将我父亲违抗命令,不听指挥的情形告到了蒋介石那里。蒋要在开封召开军事会议,解决这个问题。刘熙众请示父亲怎么办,父亲命人到参谋处将最近与李宗仁来往的电报取来检查。刘熙众翻阅一遍,果然有些词句很生硬,但这些词句都是他在来电上信手批注的,而参谋处却将这些文字原封不动当作正式电文发了出去,事先也没请他过目。父亲自知欠妥,但倔犟的性格使他不肯认错,只淡淡地说:“李宗仁要打官司,那就打吧!”刘熙众竭力劝导,请他派人去徐州,当面向李宗仁解释一下,以缓和关系。父亲沉思了一会儿,说:“好,你代表我前往解释解释吧。”
刘熙众走后,蒋介石亲自打电话给我父亲,说:“我决定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在开封开个会,请向方兄带同孙军长等务必到开封见见面。”父亲不假思索就答应了。第三路军“八大处”的处长们都坚决劝他不要去开会,主张派代表参加,但他去意已决,劝阻无效。
下午,刘熙众赶到徐州,李宗仁在升火待发的专列上接见了他。刘熙众先婉言解释了一番。李一反平时一团和气的态度,脸色很难看,时而冷笑,不置可否。刘忧心忡忡而去。
当日晚,刘熙众返回巨野,向父亲如实报告会见李宗仁的情形。父亲表示根本不在乎李宗仁的态度。刘熙众不放心,找秘书长张绍堂商量办法。张绍堂说,开封会议的通知已到,主席已决定前往出席。
刘熙众又去见父亲,劝说:“据我见李长官的神情,开封会议恐对我们不利,主席还是不去为好,派个代表去,也有缓冲的余地。”父亲说:“我已复电说到时出席,怎么能又不去呢!”刘说:“可以请个临时病假。”父亲笑着说:“你不要神经过敏,我不去更叫人家怀疑。我又没有投降日本,怕什么?”
10日,父亲偕参谋长刘书香等乘汽车,从巨野到达曹县,在第十二军军长孙桐萱的军部休息片刻。午饭后,孙桐萱、省府委员张钺及部分旅、团长随韩一行同赴柳河车站,在40余名手枪队及1个卫队营护送下,换乘一列钢甲车开往开封。
傍晚,父亲一行到达开封。
同日,蒋介石偕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自南京飞抵开封。
军统局第二处处长戴笠,偕军统局特务总队总队长王兆槐,带领十二名特务亦先期到达开封。戴笠指定王兆槐具体负责绑架行动。
11日上午,父亲偕孙桐萱、张钺等去开封图书馆,拜会先一天到汴的第一集团军宋哲元、秦德纯、过之翰等前西北军袍泽。交谈中,说起最高军事当局借刀杀人,排除异己,父亲不禁义愤填膺,滔滔不绝。宋哲元见他还是当年直来直去、口无遮拦的习惯,很替他担心,于是劝道:“向方老弟,按说我是不赞成你来开封的。到了这里,我们已然是笼中鸟,还是少说为佳。”
下午1点半,军事会议在开封南关袁家花园举行,父亲偕孙桐萱等乘车前往出席会议。
开封军事会议上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有关这方面的文章,连篇累牍,人言各殊,其中不乏文艺小说、传奇故事。即使是当时亲临现场的李宗仁、孙桐萱、吴锡祺和张宣武,在他们日后所撰写的回忆录中,对与会情景之描述也有相当出入,这显然是与各位所处的时代背景、身份地位、派系情结、价值观念、切身利益、个人恩怨及品行修养等不无关系。
无论如何,父亲确是在开会期间被蒋介石的特务绑架了。
|